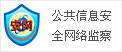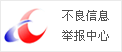年饭过后,一家人还没来得及离席,爸更是筷子都没放下,只朝妈妈呶呶嘴:"你还坐着搞么事,快给娃们发压岁钱,娃们这一杯杯的敬酒是白喝的么?" 妈得令,忙不迭地说:哦哦哦。小跑去房间的枕头底下摸出钱,家里有四个孙辈,妈一人给了一张红通通的一百元。爸乜斜着眼看发压岁钱的妈,指着身高近一米八的大孙子登眼数落妈:"做不倒个事,这么大的娃,一张你也支得出手。"妈捏着脾气说:"给多给少是我的心,你有钱你自己把得娃。" 妈这句犹如点了爸的穴,爸不会拿钱出来,妈太了解爸,但不给压岁钱的爸丝毫不会动摇他在家的地位。爸自己挣的钱用途广泛:不开工的每个早晨都上街喝小酒、吃牛肉面,遇到一起做工的好友更是以酒会友,从早上七点左右喝喝聊聊到十点回家,再提着茶碗去牌场打麻将,下午四点回家,这是他的生活开销;另外赶人情也是爸掏钱,爸的这个负荷我们子女都忙着他承担了一部分。老了,爸把自己手上的钱看得贼紧,轻易不拿出来。 妈把种地的收入、市里三套房子的租金全捏在手里,她自己不舍得花,也阻碍着爸花。爸一个季度一个季度地去市里收房租,连车费都报销不了,让爸心生怨言,但妈秉着勤俭持家的光荣使命,在我们家不论是曾经辉煌历史还是如今艰苦的岁月里,她总像钢箍一样围着我们一家,让我们家无外债,粮仓囤米,银行存钱,她让众亲友一边倒地站在她那边,让爸有冤无处申诉,只能多接着修水渠、帮村支书组织人手锄荒、给村里抽水灌苗的活计,让自己手头更宽裕些,反复细量把打牌的技术水平大幅提高些。想从妈手上拿钱,比他自己赚钱更难,反而在我爸老了老了,从年轻时走在大街上被方圆百里的人尊为"老板",到现在又练就一手瓦工匠的手艺,被人尊为"师傅",开春后,村里的年轻人一走,爸就被这方圆十里的村民们当小伙子用,谁家房屋漏雨、谁家修缮闲屋,基本上都找爸,爸是个实在人,他时时承包了小工程把自己的工钱都搭进去了,仍搞得热火朝天。爸说比起村里他同辈的、曾是他帮着扶丧的那几位,他不知赚了多少。 妈常劝说爸趁现在还能动,得省着点,防止不能动的时候要用钱。爸说已然老了,钱要趁早花,不能动的时候没本事花,没钱了还有孩子们。我们一方面表扬妈持家有方,一把年纪了还一手操持着把家里的平瓦房改建成了三层小楼,后院的闲置房屋也顶得上市里三房一厅的屋子;一方面从内心深处更喜欢爸对生活的豁达态度,爸的一辈子大起大落,但我却从他身上找不到低谷,所有的起落都是别人眼中的,他过着他的生活,不入世也不出世,活在世俗中,也能文艺地戴着鸭舌帽闭着眼晃着脑袋拉一曲胡琴,甚至在去年还怪妈买的衬衣为何不是裙子。 而妈则把钱这里藏,那里藏,又说全部让我保管,我说有多少,妈不开口。前两年我在家无意中提出农村的葬礼一定要改改,要从简,还把名人蒋勋安排他母亲的葬礼拿出来打比。简朴了一生的妈极力反对:"我看了人家那么多的歌舞,戏台子,洋鼓洋号,都是白看的么,人家怎么办的,咱也得照办。你们不舍得,我掏钱也要办得风风光光,这是一个人的最后一桩事,看你们哪个敢马虎。"妈这话像钉子一样钉在我们的心头。果然,现在妈不提让我替她管钱的事,她只偷偷告诉我:家里的柜子别轻易动了。 |
| 热门搜索:网页游戏 火箭球赛 热门音乐 2011世界杯 亚运会 黄海军演 |  |
||||
父亲母亲
时间:2017/3/1 8:42:34 点击:
|
|
作者:634233293 录入:634233293 来源:原创
相关文章
- ·河北省唐山市滦州市雷庄镇一村委会主任崔某破坏耕地破坏营商环境
- ·膏滋膏方生产加工-专注各类天然食品贴牌定制有研发团队厂家
- ·特膳膏滋 减脂瘦身食品贴牌代加工华源晨泰有研发团队服务商
- ·胸腺蛋白肽提高抵抗力增强免疫力固体粉OEM贴牌代加工服务商
- ·减肥塑身降脂,健康苗条身材洋葱咀嚼片OEM贴牌代加工服务商
- ·OEM贴牌厂家:奶饱宝催乳增乳提升母乳质量,你只差这一步!
- ·特膳金菊粉清火排毒消炎食品贴牌代加工服务商怎么选择?
- ·竹间智能1+4新产品体系亮相,为企业打通大模型落地最后一公里!
- ·膏滋的生产公司 认准华源晨泰,膏滋OEM/ODM源头厂家
- ·山楂六物膏纯手工熬制成人儿童脾胃调理滋补膏滋OEM贴牌代工
- ·叶黄素片 黑枸杞蓝莓叶黄素酯VC片 压片糖果决明子片剂OEM贴牌代工
- ·国内外盛赞!iCAR上海车展收获超高人气
- ·前所未有,卓尔不凡,iCAR 03定义全路况电动SUV
- ·iCAR 03搭载太阳能充电系统,这才是真正的追光者!
- ·登陆2023上海车展,iCAR 03创始车主全球招募
- ·特膳维生素D+钙咀嚼片贴牌代加工 均衡营养助力成长均衡营养
- ·如何选择功能食品贴牌OEM定制厂家?实地考察必不可少
- ·华源晨泰:“肠”年轻,从1杯“益生菌果蔬发酵饮”开始
- ·粉剂固体饮料OEM代加工厂家 贴牌定制 一站式服务
- ·特殊膳食日本配方酵母抽取物美肤片全身白片剂OEM贴牌代加工
相关评论

发表我的评论






























- 大名:
- 内容:
本类热门
- 07-04·幼时遭“狼舅”拐卖 21年后终找到双亲回家
- 12-17·街头开凯迪拉克“被撞” 一口要2万
- 07-04·县委书记疑抄袭文章 官方已介入调查
- 08-10·上海现黑恶装修公司 栩采实业 无资质 被叫停工后欲勒索5400万元
- 07-03·毕业季因多种原因被花样扣毕业证 学生该如何维权?
- 04-25·手机号背后的暴利:有人靠炒号身价过亿
- 07-04·野生动物园东北虎哺育成活7胞胎 全球罕见
- 11-14·68年来最大!今晚去看“超超级月亮”错过将再等18年
- 07-21·复盘CBME,4大关键透露了奶粉发展新趋势
- 07-04·'电商客服帮退货' 警方追回20余万
本类推荐
- 10-01·《快乐大本营》国庆精彩不断 邓超跪地何炅变身
- 10-01·徐洁儿节目秀睡衣 坐镇《生活魔法师》气场足
- 10-01·2011东方时尚电视模特大赛全国总决赛上海落幕
- 10-01·第六届央视舞蹈大赛将收官 舞林高手巅峰荟萃
本类固顶
- 没有